With Apologies to Mom, God, and a Bunch ofOther People I Never Met/致歉人
原作:undertale
作者:Polyhexian
配对:Frisk & Sans ; Alphys/Undyne
等级:Gen
翻译:阿息
原作地址:戳我
授权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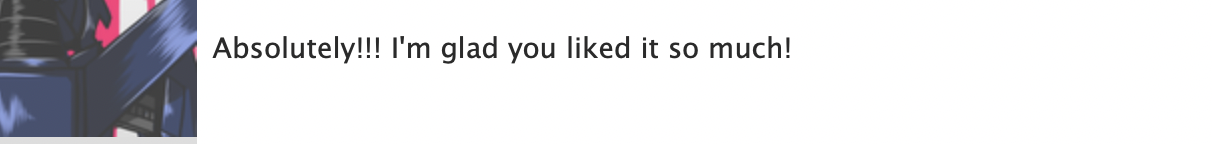
你患了夜惊症。
你在梦里伸出双手翻搅尘埃,脸颊因微笑过久而僵硬不堪,你感觉到匕首紧贴在裤腰处。整个世界空洞如你。
在噩梦与清醒之间,Chara 对你的灵魂喃喃低语,哀求重生,渴求怜悯。求你了,Frisk,我只是想活下去,我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就够了,求你了 Frisk,让我借用你的身体,就一会儿,我想再次尝尝妈妈的馅饼就好,我想向她道歉,求你了 Frisk,可怜可怜我吧。
你挥舞着拳头醒来,一如往常,但是你尽己所能克制住自己的攻击,只是把拳头徒劳地戳进他的肋骨,对方毫发无损,而你浑身乏力,指节上由于之前独自入睡时胡乱攻击造成的结痂还未脱落。
他也醒了,醒来的方式跟你一样暴力,一身白骨狠狠压进床垫里,床单仿佛湿透的纸张,轻易撕裂开来。你艰难地拽动膝盖,躲闪后滚,落地时你的第一反应毫无理智可言,脑海里闪过的念头是——你又要去买新床单了。
你跪在那里对上他的眼睛,他已经半个身子探出床外,攥紧手指,白骨森森停在半空,小束的蓝色微光颤搐着环绕四周,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喉咙上他拳头的力道,几乎克制不住般,紧紧逼在你的颈静脉。
你们俩都在喘气。
须臾无限漫长,你只是坐在原地,盯着他那只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瞳孔,直到他终于找回理智,眼睛恢复成平常那副令人安心的白色针点,拳头逐渐松懈下来。
于是你重新爬上几乎已经不成型的床垫,垫子里弹簧已经失效,所以就跟坐在地板上没什么差别,你把不经用的床单推到角落里,嘴里开始念念有词。
“现在是十一月七日,”你开口,“我们来到地面已经过了五年,大家都还活着。Papyrus 在楼下的另一间卧室里。这里是你家。我不会重置(reset)。”
“你的名字叫 Frisk。”他叹息着靠过来,手指戳进你的夹克背面,尽管妈妈一直让你别穿夹克睡觉,然后你将脸埋进他的 T 恤,呼吸着魔法散发出的木炭和糖的气息,你紧紧闭上眼睛,继续安静地听着,“在这个时间线你没有杀过任何人。你每件事都做对了。Chara 没办法得到你。”
你蜷起身体就像一面盾牌,你可以感觉到骷髅毫无意义的呼吸落在你的发际线上,“而且,我不讨厌你。”他最后说。
你于是终于可以让自己的喘息平静些许。
“我永远不会再重置了。”你低声说,你的嘴被布料堵住了,所以他可能没有听到你说什么,但是这是稿子的一部分,所以他应该知道你的意思。
最后,终于,他慢慢松弛下来,就好像是真的而不是他装出来的那样,就好像你无法在近在咫尺里感觉到他骨髓里颤抖着的紧张和恐惧似的。
你从未在白天这么难受过。
白昼天光大亮,阳光普照,你可以轻易忘记 Chara,忘记 Chara 用你的双手对你自己和你所爱的人做出的那些事情。在白天,世界是温柔且和煦的,而在黑夜,连绵不断的黑暗咬住你容易动摇的疲惫灵魂,逼迫自己回忆起来。
你从来都睡不安稳。
Sans 也从没睡好过,其实你一个人在妈妈家里会睡得好一些,你很确定,他也是独自睡更好,毕竟没有那么多尖叫,也没有人会试图杀死对方,但是你很清楚,当你在妈妈家过夜时你会抽泣着醒来,而恐惧并不会消失。那种恐惧时时刻刻攀上你的脊背,攥紧你的心脏,你的魂魄,你的声音,你受够了,你在见到 Ebott 山峰之前产生过那种冲动——让这个世界没了你也继续运转吧——现在这种冲动又回来了,而你需要,需要这样做,你需要有人来提醒自己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你需要有人真正深刻地理解你的痛苦,发自肺腑地了解你到底怎么了。妈妈她不会理解你。
虽然,你多么希望她能理解。
你知道,她觉得 Sans 在占你便宜或者你们在做一些十五岁年纪不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你并没有,你一点也不想告诉她,因为你完全不想承认。你不想跟她谈这个,你不想解释为什么你这么做。你不想告诉她你看过她的尸体化作灰尘沾在你的鞋子上是什么样子。你做不到。你不会这样做。她不会理解。你不想让她理解。你不想让她也感受到你和 Sans 遭受的同样的痛苦。
终于,你的呼吸平静下来,随着每一次颤抖的叹息,你的恐惧就减轻一点。柔软和熟悉的现实重新充满你的意识,回到现实令人安心。
你靠在他的肋骨上重新睡过去,祈祷着也许某天你不再需要这样做了,但是现在你需要,所以你很高兴你有他在。
~*~
秋高气爽的下午,你步行去公交车站,结满霜冻的草叶在你的鞋下沙沙作响,像满地踩碎的玻璃。你很快要满十六岁了,Papyrus 说要去教你开车,最近你在网上看哪款车合适,妈妈和 Asgore 还有 Undyne 都说不管你看上什么车他们都会凑钱来帮你买,哪怕你的大使职位确实薪水不菲。Alphys 甚至说她会升级一些功能让车看起来更酷,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要那么光鲜亮丽的车子——也许一个小面包车足矣,这样你就不用担心 Asgore 的羊角了。但不论如何,你还是很感激她的提议。
你一边过马路一边查看手机上的照片,并没有注意到那辆雪佛兰 2004 Cavalier(你在凯利蓝皮书上见过这款,你喜欢它的耗油量和价格并且在认真地考虑选它或者它的同款),等你注意到时已经太迟了,你正进入南向车道而车子的速度太快,你看到绿白相间的公交站牌就在街道对面,你看到一对受惊的情侣在街道对面晃了晃头,此时,Cavalier 的轮胎摩擦人行道发出刺耳的刹车声,然后撞上了你。
你的灵魂受到巨大的冲击而开始灼烧起来。
~*~
在你们逃出地下世界之后,你曾经重新读了两次档。
第一次,你几乎是出于无私的理由。在某次政治性质的讨论会中,你其实不太理解这次讨论的内容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你都甚至想不起来你建议了什么,而最后的结果是你的提议终结了整个讨论。于是你重新读档回到那天早晨,重新来了一次,这次效果不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那之后 Sans 整整两天没跟你说一句话。就在你快要崩溃恳求他的原谅时,他出现在妈妈家门口,带着一盘 Groundhog Day 的碟片,微笑着坚持要举行一个小小的家庭电影夜。他没有提关于那件事,但是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
至于第二次,你想不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因为这一次残酷的是你。你连想都不愿意想起来,但是这是最后一次,没有下一次了。
彼时 Sans 在网上认识了某个女孩,而且似乎真的对她产生了好感。在她过来拜访的时候,你被请出了房子,不得不呆在妈妈那里。那天你晚上做了噩梦,他的血沾满你的双手,这段记忆使你惊醒过来。
你怒不可遏,怒火中烧,以至于你载入了一周前的存档。
你回到了一周前妈妈的房子里,在一时的得意之下,你觉得他活该,你感到病态的痛快和骄傲,之后便是铺天盖地的内疚袭来淹没全身。你花了十分钟趴在马桶呕吐,几乎呕出你的肠子,直到你听到他的球鞋踩在楼梯上,球鞋,而不是拖鞋,你知道你搞砸了一切,然后门被砰地推开,他那般愤怒的样子你只在其它时间线上见过。
你悲哀地看着他,转头对着半夜的马桶抽泣不止,呕吐物粘在你的头发上,他的表情柔和下来,你都不知道他可以这般温柔,于是你们俩就坐在浴室地板上耗过了剩下的夜晚。你终于吐完的时候,他将你的头发从脸上拨开,你对他说对不起,说了一遍,只有一遍,然后他说他知道。
第二天早上,他下楼帮妈妈做烤饼,然后你开始洗澡,用力搓洗身体试图把内疚和自我厌恶感从自己的皮肤上洗掉,直到皮肤红得跟你的灵魂颜色一样,但是没用。内疚洗不掉。
这一次,你站在阳光下,重回新生。光线温暖地抚摸着你的头发,蓝天万里无云。
头顶的天空微笑着望着你,你一时无法确定身处何方,你环顾四周看到路边到处是白色的塑料折叠桌子,上面堆满蜗牛派和水香肠做的汉堡,然后你忽然想起来,这是重回地面第五周年的庆祝会现场——当时你几乎是下意识的存了档,因为你看到大家都如此开心,你希望把这一刻永远保存下来。
你看到 Mettaton 那一组正在场地尽头的舞台上玩着一些你记不清楚的游戏,Shyren 的歌声飘散在混杂的人群中,妈妈和 01 正在鼓掌,Alphys 和 Undyne 在草地上跳什么荒唐的舞蹈,但是 Alphys 不太合作,因为 Undyne 总是偷偷亲她让她双脚腾空。你不太记得 Sans 在哪里,但是你仍然能感觉到车子呼啸而来的冲击撞碎了你的骨头仿佛在皮肤下面有无数牙签刺穿然后——
你身后传来喀拉一声,你痉挛着转过身,整个人仍然非常困惑,然后你看到了他,他正站在食物棚子底下,双手握拳放在身侧,你注意到有微小的蓝焰痉挛着,一半食物的纸盘落在脚边。他盯着你,眼眶中燃烧着杀意,而人们都围观着窃窃私语。你甚至无法移动,四肢百骸都被锁在当场,他几乎没有克制眼中的愤怒,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一把抓住你的手,大家盯着他把你拖进停车场,拖离派对里的视野范围,不过没人跟过来。
“你,做,了,什,么?”他嘶嘶地问,扔下你的手,再次握拳。实际上,你可以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悲痛和恐慌,你厌恶自己又一次对他做了这种事。你承诺过的。你明明承诺过的。
“对不起——”你结巴着,无法对上他的眼睛,“我不是——那时候——我没有注意到——”
“你不小心重置了?”他责备道,他看起来如此愤怒,你从来没见过他这般愤怒的样子。至少没有在这个时间线上。
“不!是的。我没有重置。”你说着,盯着自己的双手。手上没有血,毫发无损,“我觉得——我觉得我死了。”你不确定地说。
他僵住了。
“噢,”他说,“噢。该死。”
“不,不——”你说。
他的肩膀垮下来,眼睛熄灭,恢复寻常。
你继续往下说:“不,我——我很抱歉,我不是——我没有——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忽然就重新读档了,只是——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对不起——我知道,我们不是朋友,我不是故意的,Sans,我——”
你们几乎一样高,于是在他瘫坐在地上之后你跟着他这样做了,你绝望地坐下去,害怕他再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该怎么办。
你们就这样一起坐在温暖的沥青地上,额头抵着额头。
他在颤抖。
“该死,你当然会那样想,”他低语,“孩子,不,我们——我们是朋友。我不应该发这么大火。”
“我承诺过不会再读档的。”你说着,感觉到泪水涌了上来,但是没有眼泪落下,“我明明承诺过。”
“是的,我知道,”他说,手指在地面上抠出划痕,你能听到骨头钝重的刮擦声,你在想那是不是很疼,“这只是个意外。没关系。”
你颤抖了片刻,直到你听到有脚步接近,你退回身,擦着鼻子,他将手伸进裤腿假装在玩手机,直到路人走远,他站起来,向你伸出手。你接过他的手。
“我们去吃些热狗吧,好吗伙计?”他说,然后你默默的点头,悲哀至极。你重新回到现场,妈妈能看出你心情低落,但是你无法告诉她为什么。
那天晚上你在妈妈家过夜,她看上去很高兴。你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自己的床了,你几乎忘了那张床有多舒适——柔软的床垫和床单,一条真正的羽绒被,你喜欢的记忆枕,以及一切。床上摆满了妈妈给你买的玩具动物,你轻轻把它们挪走,因为太多了,你不想把它们踢下床,你需要钻进被子里。
你抱紧枕头,尽管夏夜温暖舒适,你仍然在黑暗里颤抖不止。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了一下,你希望可以无视它,但是你不能。
“你来么。”
上面显示,来自 Sans。你想拒绝,但是你不能。
你抓紧手机,希望入睡,但是它在十分钟之后又震了一次:“我没有生气。”
他生气了。你知道。他当然生气了。他怎么能不生气呢?他应该气极了。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试图安慰你,仍然给你那些勉强的好意,一如往常,因为他知道,你能轻易毁掉他的生活,他知道你能杀了他,杀了每个人,你甚至能因为心血来潮,一时兴起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送回地下世界。
他在恐惧你。
老天,他怎么能不恐惧你。你本来就是个怪物,真正字面含义上的怪物,在你遇到一个真正的怪物之前。老天,你甚至比怪物更糟。你是人类。
你的手机又震了一次。
你选择关机,把手机塞到床边,把脸狠狠埋进枕头里,试图停止噎在喉咙里的抽泣,你早就过了哭泣的年纪。
“不,”你脑袋里厌恶的声音回答道,“快过去吧,也许今夜他醒来终于会杀掉你,那不是公平多了吗!”
你在胃疼,眼睛发胀,你无法通过鼻子呼吸,鼻塞得厉害。你在枕头里颤抖着,试图堵住大脑里越来越响亮的声音。“去吧,去杀了他,重新读档,也许之后他就会明白你为何这样做,也许之后他就不会如此厌恶你了!噢,我在骗谁呢,他恨你,不是吗?你们当然算不上朋友了,没人会跟我们这种人交朋友的,Frisky,除非他们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好处,而他确实也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不是吗?他会继续假装关心你,只要你不去杀掉大家,这不是很公平吗,Frisk?这不就足够了么,Frisk?这不就是你应得的么,Frisk?”
你站起身。
你穿上鞋冲下楼梯,妈妈坐在她的桌前,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九月新学期备课,她抬头透过眼镜看你,你走下铺着地毯的楼梯,站在门厅的实木地板上。
“Frisk,我的孩子,你没事吧?”她说,你知道,她能看出来你并不好。
“我去 Sans 家。”你说。然后,她很受伤,你能看出来,但是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你讨厌对她撒谎。她站起来,走过来拥抱你。
“好的,Frisk,”她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妈妈。”你说,伸手环住她温暖的毛茸茸的脖子。她松开手。
“你希望我开车送你吗?”她问,但是她知道答案。
“不,”你说,“十分钟就走过去了。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
“好吧……”她说,为你开门,外面星空闪耀,“注意安全,我的孩子。”
你走进夜色中,朝 Sans 家的方向走去,直到你转过街角。
你知道从这里开始妈妈再也无法从窗户那边看到你的身影了,于是你转身,开始走向另一个方向。
~*~
你经过公交站,颤抖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停下脚步。
你只是继续行走,不停行走,直到大脑里 Chara 的声音逐渐疲惫变得安静下来,你站住了,俯瞰着眼前的山峰——那不是 Ebott 山,只是沿路看到的普通风景,山峰侧面悬崖高而陡峭,危峰兀立,怪石嶙峋,让你感觉紧张,因为悬崖边的木栅栏看起来是那样脆弱,Sans 通常喜欢斜靠在栅栏上欣赏风景。
现在你倚在其中一根栏杆上,俯视着潜在的坠落可能。这里非常高,你确定人类掉下去肯定会致命,但是你现在已经在一些诡异的事件中幸存下来了,所以你也不确定。你的右手边有个停车位,登山入口已经很近了,你走到停车位旁的长椅坐下来,椅子上的潮气让你不舒服,清晨的露水已经开始渗入木材。
你把目光从山峰上移开,仰头,望着头顶的星空,你一直为此感到震撼——视野中没有被光污染玷污的天空广袤无垠。
你思考着,如果你死了大家会多难过,这是个坏主意,你努力让这个念头说服自己,因为你知道这一切会有多糟糕。妈妈会崩溃的。Alphys 从来都不擅长处理哀伤的情绪。甚至也许连你的亲生父母也会忧虑万分。
然而,此刻,这画面如此模糊不堪,因为你知道,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胁,你会毁掉他们的生活。
即便你想停止重置,你也无法做到这点。因为你不想死,所以你不会死,你自动读档重来。也许到最后,每个你爱的人都会变成 Sans 那样——他们开始记起来了,比他们现在的记忆更多,他们会在每晚的尖叫和哭泣中醒来,害怕孤独,恐惧靠近任何人,草木皆兵。
你不确定你死之后会去哪里。Chara 明显没有去成任何地方,考虑到那家伙一直在你脑袋里尖叫着让你放弃控制权,教唆你,如果真的失去活下去的意志那就让 Chara 来接手一切吧。你短暂地思考了一下,你和 Chara 会去往同一个地方吗,或者 Chara 会不会还是 Chara,或者记忆,或者变成你,或者变成其他东西。你几乎想要这样做了,只是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你究竟会去哪里。
你蜷缩在长椅上,戴起兜帽,胳膊放在太阳穴下面,闭上眼,你想着这个睡着了。
~*~
光线从殿堂的窗子渗透进来,你可以听到鸟儿欢唱,微风轻拂。风和日丽的一天,他又出现在那里。他将会杀了你。你知道他会的。你也要杀了他。当然,你其实并不是那么希望让他去死,你更想跟他决一死战,你享受的是这个过程,毕竟他是你最大的乐趣。
你的头发沾满尘埃,你的心中充满恨意。
他先出招,疾风裹挟着骨头和爆炸袭来,你轻车熟路地躲开,就像舞步,一场你已经跳了千百次的舞步。你躲开了,他不太高兴,哪怕他脸上挂着的微笑万年不变。暴力的冲击跟随他的手指和眼睛的指示铺天盖地袭来,每一次你都能够刚好避开,在柱子和石头之间的光线中交锋,仿佛你可以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永远。
他开始感到疲惫。
他向你伸出双手试图给你一个拥抱,你攥紧了手中古老的匕首,手中的触感熟悉而舒适。
然后。
你从长椅上滚落,摔在柔软的泥土上,你大口呼着气,抠挖地上的泥土来对抗脑中回响的尖叫,这声音比平常更响亮,更愤怒,更绝望。你花了好几分钟让它安静下来。
之后你终于坐起来,抖落身上的尘泥,眺望眼前的风景。现在破晓降至,天空呈现出奶油橘粉色,模糊氤氲的雾气环绕山峦。你看了一会儿,然后爬上长椅,脱掉鞋子,小心地放在地上。
你朝木栅栏走近一步,深深吸了一口气。山间拂晓的空气哪怕在八月也是冰凉易碎的,你可以尝出清晨的露水和隐约逼人的燥热气息。
你翻过围栏,站在悬崖边上,脚趾因为袜子里的草叶而蜷曲。
如果你不想死,那么你不会死。你有经验。但是,如果你下定决心,你下定决心要消除对朋友幸福的最后一丝威胁,那么你会甘愿死去。你知道的。你能感觉到灵魂里的决心,沉默而笃定,就如同你能听到 Chara 此刻的尖叫声盖过了树木的涛声。你长长的深呼吸,今天并不是风和日丽的一天,但是总体而言,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很美好,你从生活中得到了远超你期待的东西——真正充满爱意的家庭,一群真正为你着想的挚友,也许那就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你闭上眼。没事的。这样做没事的。你没事的。
“frisk!”
你猛地一个激灵,被突如其来的叫声吓到,转身看到他。他就在那里,看着你满脸写满极端的恐慌,他恒久不变的微笑表情变成了深深的皱眉,那是他最接近悲伤或者恐惧的表情。他猛地伸出手,哪怕在那么远的地方根本什么都够不着,他仍然伸出手,就像他即将用魔法抓住你一样,但是你受到了惊吓,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脚下一滑,柔软的蓝天就在身体上方,什么都没抓到。
你倒下去的最后一个念头只剩下你必须得给出解释,然后灵魂开始灼烧起来。
“frisk!!”
~*~
你再次回到了阳光下,空气里有音乐飘散。这一次你知道自己回到了哪里,你不需要适应的时间,直接转身就找到了 Sans。
他再一次打翻了自己的纸盘,但是这一次他看起来并没有生气,而是结结实实吓到了。你能看见他的手在颤抖,人们再一次围观。你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又一步,然后你开始奔跑。你跑到了停车场,他从背后抓住你,紧紧把你抱在他胸前——他肯定是为了抓住你而走了捷径。
你胡乱踢腿,挣扎,但是他只是抱得更紧,你无法松懈下来,直到你听到他接近哽咽的声音。
“孩子——”他说,当你终于肯平静下来,“What the fuck?”
你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但是你无法转身看他,你现在词不达意,张开嘴的第一个词只有“对不起”。
他的拥抱更紧了,你的手抵在他的前臂上用力,指关节泛白,你只是不停地道歉着,哪怕你并不想。你无法说出任何其他话。你想不出任何其他话可说。
你明显是怎样都平静不下来了,于是他直接把你抱了起来,就像你小时候经常会做的那样——紧贴着大家像个一动不动的树袋熊——你将脸埋进他的肩膀,然后颤抖着不自觉的道歉着,没有落下眼泪。他就这样抱着你走捷径回了家。他的家。家。
你感觉好些了,你困惑沮丧地坐在没洗过的床单和一团糟的床垫上,讨厌这样的自己。你实在筋疲力尽,无法僵持更久,你靠着他的肋骨松懈下来,仍然抽噎着,像个小孩子一样打嗝。
“为什么?”他问,但是你无法直视他。
“对不起。”你又说。
“我打电话给 tori 问她你是否还好,你没有给我回信息,”他的声音发颤,“她说你来我家了,而我——老天啊孩子,我就知道,呃,我找不到你,不管去哪,我们给大家打电话,每个人——我觉得,我觉得我太迟了,然后我——我——”
他跟你一样浑身发抖。你搞砸了。
“对不起。”你说。
“你在想什么?”他说,捧起你的脸看他。你张嘴,你不知道说什么,但还是艰难地开口。
“我觉得,”你嘶哑地说,“我觉得,如果我死了,我就不再是你们的威胁,我不会再受到诱惑去——去重置——我只是——我爱你们每个人,如果——我觉得,只要我不存在了,就在此时此刻,那么我将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大家就不会再害怕我——”
他脸上掠过的惊骇让你失声。
“你确实没把我当作朋友,是不是。”他说道,声音如此微弱你几乎听不见。你没有摇头的力气,只是把脸更深的埋进他的胸膛。
“我知道你在怕我,”你说,“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让我来你家过夜,哪怕你根本不想看到我。我知道你醒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人是谁,而我就在这里,我知道你讨厌这个,”你结巴着,“我知道你只是想让我开心,因为你知道我可以对你做什么,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我无法像这样活着了,我不想变成那个你恐惧的人,我不能——我不——我不能够——”
“对不起,”他最后开口,你收紧了手中的布料,“我不擅长很多事情,孩子。不擅长科研,不擅长当个好哥哥,也不擅长做个朋友,或者负责任的成年人,或者——”他沉默片刻,“不擅长很多事,只会他妈的搞砸这些烂摊子,我想。”
“你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骂脏话,”你脱口而出,他嗤笑着,意外的露齿而笑。
“对啊。不是骂你。”
你一时语塞,但是现在,你没有像之前感觉得那么糟糕了,至少。“你是吗?我是说,你怕我吗。”
他思考了半晌。
你很感激他这么做,因为你想要一个诚实的答案,而不是空洞的,只是为你好的安慰。
“没错。”他最后说,“但是我宁愿再经历一百个时间线也不愿意看你自杀。拜托不要再做那样的事了。”
他继续说着,“我从没有意让你那样想,让你觉得我关心你只是因为我是被迫的,之类的。你是家人,孩子,真正的家人。你觉得,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害怕的人吗?我曾经看过 undyne 刺穿你的身体,我曾经见过 asgore 进入神级模式——见鬼,孩子,我曾经在某些时间线上见过你根本没能够走出废墟,而且我知道他们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傻,我——”他停住了,皱眉,抬手抓住自己的胸口。
“我一直害怕自己有一天醒来,而你躲得不够快,我将会再次看到人类的血液是什么颜色的。我不想那样。我怕的是那个。”
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你决定闭口不言,只是对着他的 t 恤叹息,你可以感到你的呼吸穿过了他的肋骨。
就在沉默开始变得疼痛时,你终于开口:“我不会再那样做了。”
“谢谢。”
“那……现在怎么办?”你问,“我们重新回到那种状态吗?不管那是什么?夜惊症,试图在梦里杀掉对方?”
“也许你得再试试在 tori 家里过夜。我的意思是,慢慢一步步来,我不是说冷火鸡疗法或者什么的,但是,也许这应该是个目标。现在这种互相依赖的自毁倾向,不能再继续了。”他说着挥了挥手,你点头,“你有我电话。如果 Chara 再弄醒你就给我打电话吧。”
听到这个你感到安心了一点,你点头,因为听起来不错。有个目标总归是不错的。
“我会尽量不那么严厉地对待你读档的事情,好吗?这个——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我想的那么严重。我希望我们都可以从这堆烂事里扛过来,所有人,但是死亡——死亡完全是另一个领地,棒球地,墓地。管它什么。”
你被他漫不经心的冷笑话而逗笑了,哪怕压根毫无道理,根本不好笑,直到这时你才意识到自己没在哭了。眼睛已经干涸。
“我们是朋友,孩子。我们是一家人。就是这样。我很高兴认识你,不管有没有重置。甚至在我得知你是异常之前我就很高兴认识你了,好吗?”
你点头,叹了口气,感觉疲惫但是已经好多了。
“以防万一——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读档回到先前那会儿,我们可以去现场享受派对,像我们第一次那样,好不好?”
你思索了一会儿,以防这是某种测试,你不能令他失望。
你深呼吸,最后点了点头。
“从十倒数,好吗?”
你往上看,他的微笑这一次是真诚的。你深呼吸,进入脑中的菜单。他慢慢倒数着,当数到一的时候,你闭上眼睛,读档重来。
END